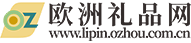一个“安史剧官”的漂白史
唐德宗朝,吏部侍郎邵说有望入相。金吾将军裴儆明确反对邵说拜相,认为:“(邵)说与史思明父子定君臣之分,居剧官,掌兵柄,亡躯犯顺,前后百战,于贼庭掠名家子女以为婢仆者数十人,剽盗宝货,不知纪极。力屈然后降,朝廷宥以不死。”裴儆指出了邵说的历史污点,即邵说在安史之乱期间出任大燕伪政权的“剧官”。如此确凿、严重的历史问题,沉重打击了邵说的仕途,邵说最终未能更进一步、跻身宰辅行列。
既为“安史剧官”,求诸典籍,邵说却仅在两唐书留有篇幅短小的传记,以及若干篇署名文章,与他“剧官”身份完全不相称。两唐书《邵说传》对传主的前半生一笔带过:
 【资料图】
【资料图】
邵说,相州安阳人。举进士,为史思明判官,历事思明、朝义,常掌兵事。朝义之败,说降于军前,郭子仪爱其才,留于幕下。累授长安令、秘书少监。德宗朝,迁吏部侍郎、太子詹事,以才干称。
邵说,相州安阳人。已擢进士第,未调,陷史思明。逮朝义败,归郭子仪,子仪爱其才,留幕府。迁累长安令、秘书少监。
涉及邵说生平的第三份重要文献为其自书的《让吏部侍郎表》,概括他反正后“再忝柏台,四登郎署,宰理京剧,倅贰秘书”。三份文献对附逆经历都多有隐晦。邵说“在职以才显”,延续了中唐文人词臣以才华吏干仕进的路径,平步青云至吏部侍郎。那么,问题来了:邵说这位“安史剧官”在安史之乱中有何经历,如何作为?他如何摆脱附逆历史的影响,显达于唐廷?安史之乱期间及之后存在一个类似邵说的官员群体,他们曾出仕安史政权后又归降唐朝。该群体入唐之后,如何处理两种身份的矛盾,社会舆论如何评价他们?邵说的微观人生蕴含着怎样的时代信息,隐藏着何种历史深意?
一、邵说是如何附逆的?
邵说为寒族子弟,祖父未仕、父亲邵琼之为殿中侍御史;天宝年进士出身,守选期间即遭遇了安史之乱。《让吏部侍郎表》自陈“陷贼”经历:
适会老母弃背,服丧河洛。及禄山之至,礼制当终,臣愚不脱縗麻,更逾再岁,而贼中言议,往往纷然。臣惧凶党不容,寓游洛魏,值庆绪奔遁,保于相城,大搜词人,胁为己用。以凶威责臣不至,以驿骑逼臣遂行,与潘炎始陷凶逆。
至德二载(757)正月,安史政权内讧,安庆绪谋杀父亲安禄山自立。九十月间,唐军先后收复两京,安庆绪仓皇出奔相州(治安阳)。其时,邵说在安阳服母丧,在叛军驿骑的“逼迫”之下委身安庆绪阵营。安史之乱期间,官僚士人“为贼污者半天下”,有的人是在大唐朝廷中郁郁不得志,有的人贪慕大燕政权许诺的荣华富贵,有的人判断天命转移,安燕王朝即将取代李唐王朝,种种考量使得附逆投贼者蔚为大观。无论是出于某一种或某几种考虑,邵说终究选择加入叛乱阵营。
近年来安史之乱研究的深入和唐代人物考释的发达,为我们勾勒安史阵营内部的次级群体提供了可能。现有材料表明存在一个包括邵说、王伷、张献诚等人的小团体。安史之乱中期,他们都意图背叛安庆绪、转投史思明;安史之乱后期,他们都反正归降;入唐之后,他们都自述“身在曹营心在汉”,被迫附逆,且暗中破坏叛乱。
安庆绪弑父自立、兵困相州,声望与实力江河日下。雄踞河朔、首鼠两端的史思明在叛军阵营中后来居上。邵说等人便在此时倾向于以史思明取代安庆绪。乾元二年(759)初,史思明杀戮安庆绪势力,再次反唐。安史之乱进入第二阶段。邵说自述:
遽闻思明款附,燕赵服从,欲取黄沙岭路,因此得归阙下,属思明数万之众,南镇赵州,送臣于范阳,抗疏以闻奏。肃宗特降中旨,授臣左金吾卫骑曹将(参)军,宣恩命示:闻卿远来,可且于思明处憩息。
王伷亦非世族子弟,天宝初年中进士后投身宦海。安史乱发之初,河南道采访使郭纳投降叛军。王伷为其支使,随之投降,参与“宣慰”河北州县。对于安史交替,《王伷墓志》(《唐故太子赞善大夫赐绯鱼袋琅邪王公墓志铭并序》)记载:“禄山子庆绪走保相州,又为所胁受职,乃与友人邵说间行诣史思明于幽州。时史思明以所部归降,而公得以投焉。朝庭嘉其忠节,诏拜东宫文学。”
张献诚出身将门,父亲张守珪曾任范阳节度使,对安禄山有知遇之恩。安禄山拜张守珪为义父。张献诚与安禄山关系自然较为亲近,为安氏表请为檀州刺史。叛乱前,安禄山颇为知人善任,提携、笼络了不少人才。这些人或参与安禄山叛乱,或对安禄山感佩在心。《张献诚墓志》(《唐故开府仪同三司检校户部尚书知省事赠太子太师御史大夫邓国公张公墓志铭并序》)撰书于乱后多年,依然明言“时幽州节度使表请为檀州刺史”。对于附逆叛乱一事,墓志曲笔:“公所悲侯印犹在虏庭,乃于邺中与王伷、邵说、崔溆等相约而言日:潜归圣代,贤之之节;耻饮盗泉,高士之志。今请逃于寇难,誓比骨肉。及随肩之时,为追骑所困,遂絷于思明之众也。然肃宗清华夏之岁,思明蓄横猾之谋,有诏遥授公卫尉少卿,旌其善也。”
根据三人墓志可知,王、张与邵说相聚于757-758年岁末年初的相州。三段文字都强调了三人归顺朝廷之心。张献诚墓志尤其明显,言之凿凿小团体相约“潜归圣代,贤之之节;耻饮盗泉,高士之志”。不过,三人阴差阳错投入史思明阵营的经过,邵说之词较为详细,王、张二人一笔带过。细究其词,大有蹊跷。邵说“欲取黄沙岭路”回归朝廷。“黄沙岭路”为交通河北、山西的太行隘口之一,地处赵州赞皇县。隘口与地名至今仍存。从安阳经黄沙岭路回归朝廷,需要先北上洺州、邢州、赵州,再跨越太行山进入唐军控制的山西地区,置向东、向南等更便捷的路径于不顾。结果,邵说等人在赵州遭遇了南下的史思明,不得不再次“附逆”。为实现回归朝廷的“夙愿”,邵说舍近求远,最终向北投入了史思明怀抱,令人颇有言行不符之惑,顺带为贼所迫的描述(“为追骑所困”)也大为可疑。三个文献对此都选择性无视,转而强调史思明彼时短暂归顺朝廷的事实,以此证明主人公“间接”回归朝廷。比如,邵说的“思明款附,燕赵服从”、王伷的“时史思明以所部归降,而公得以投焉”。对于史思明的横猾之谋、狼子野心,久经政坛的张献诚等人心知肚明(“思明蓄横猾之谋”)。他们投身史氏的真相,是震慑于唐肃宗前期严厉的惩处“逆官”政策,出于利益考虑所做的现实选择。
唐肃宗收复长安之后,朝廷将“陷贼来归”的文武百官数百人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于市,次赐自尽,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贬”。于京兆府门“重杖一百”的罪臣往往杖毙棍下:“达奚挚、张岯、李有孚、刘子英、冉大华二十一人,于京兆府门决重杖死”。陈希烈等七人“自尽”于大理寺,算是恩赐;达奚珣等人在百官围观之下斩于独柳树下,体面全无。惩罚有扩大化的趋势,即便未曾出仕伪朝、仅与伪政权有所关联者,也须自首,接受朝廷的甄别;甚至罪及附逆者先人,如“发韩公张仁亶之墓,戮其尸,以张通儒故也”,这也是张通儒等安史骨干与朝廷顽抗到底的重要原因。
环境如此肃杀,邵说即使有归降之心,也不得不忧虑自身安危。唐军收复两京之初,叛军人心动荡,“闻广平王赦陈希烈等,皆自悼,恨失身贼庭;及闻希烈等诛,乃止。”“会三司议伪官罪状至范阳,思明谓诸将曰:‘陈希烈辈皆朝廷大臣,上皇自弃之幸蜀,今犹不免于死,况吾属本从安禄山反乎!’”(《资治通鉴》)面对长安朝廷血淋淋的屠杀和日益衰败的安庆绪,投靠游离二者之间的史思明便成了邵说、王伷、张献诚等人最现实的选择。
当然,现实的利益考量不可能明目张胆地出现在奏表与墓志之中。付诸笔端,三人只能将投靠史思明与归顺朝廷强行关联,并且强调皇帝或朝廷对此种“关联”的认可与褒奖:“肃宗特降中旨,授臣左金吾卫骑曹将军,宣恩命示:闻卿远来,可且于思明处憩息”“朝庭嘉其忠节,诏拜东宫文学”“有诏遥授公卫尉少卿,旌其善也”。邵说三人所列官衔,应理解为一种刻意的突出,为投靠史思明披挂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此种表述与前述邵说等人“被逼”“胁迫”接受伪职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事实上,在唐朝中期的职官制度中,藩镇、使臣为幕僚奏授京官已成例行公事。邵说的左金吾卫骑曹将军和王伷的东宫文学、张献诚的卫尉少卿,当为史思明替幕僚奏请的带职,意在搭建朝藩之间人事流动的桥梁,未经朝廷甄别,更与皇帝的肯定、垂爱无关。
二、叛贼还是卧底?
史思明叛,战火复炽。邵说任史思明判官,为辅理政事的核心幕僚,可惜具体言行无考。王伷在伪政权仕官至中书令;张献诚曾任伪兵部侍郎,出为伪汴州节度使。
对于伪政权授予的高官厚禄,王伷墓志的解释苍白:“公苍黄于戎马之间,不得走去,卒为所执。胡人以专杀为威,而公以死无所益,不若受职而图之”,将接受荣华富贵解释为“忍辱负重”。而在《让吏部侍郎表》中,邵说将效忠史思明之事以“井陉路绝,再陷凶盗”八字掩盖,还声明:“思明、朝义负恩之际,臣亦累达疑诚。伏蒙肃宗皇帝赐臣敕书云:‘卿志士苦心,王臣励节,艺成俎豆,迹陷豺狼。顷年邺中策马归命,出于万死,臣节尤彰,忠诚若兹,不负于国。’”他们三人都在第二阶段的安史之乱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绳之以朝廷律法,难免“罪行累累”。对于此点,他们也有清醒认识。张献诚之子张任的墓志追述其父“初盗发幽蓟,为之胁从,诡输小诚,求彼大任”(《唐故蔚州刺史兼殿中侍御史张府君墓志铭并序》)。文本虽然延续了父辈的话语逻辑,“诡输小诚”四字还是委婉承认了张献诚参与叛乱的事实。
三人的传世文献继续选择性无视,快速将时间轴拉到了安史之乱末期。彼时,史朝义弑父自立,叛党离心离德、呈土崩之势。唐朝适时调整了对附逆官员的处置政策,唐肃宗停止清算政策;宝应元年(762)五月,唐代宗颁布即位赦书,宣布对“逆贼史朝义已下,有能投降及率众归附者,当超与封赏”,十一月进一步放宽政策:“东都、河北应受贼胁从署伪官并伪出身,悉原其罪,一切不问。”如此矫枉过正的政策,极大分化瓦解了叛军。邵说反正的主客观条件都成熟了。
邵说在自陈中“表功”一件:“比朝义将败,谋守河阳,臣知回纥利于野战,沮破其计。”此事当指战争后期,史朝义有意弃守洛阳,收缩兵力于河阳,改善叛军的处境。邵说故意劝谏史朝义,阻扰了这一计划的施行。这件“功劳”也写入了王伷的墓志:“宝应初,大军临东都。思明子朝义将保河阳,决谋于公。公虑其凭险守固,矫陈利害,贼竟奔走,而官军整行。”如果此事属实,邵说、王伷二人称得上是高级卧底。张献诚墓志更详细地塑造了墓主人的卧底形象:“朝义继逆,疑公携贰,遂污公为兵部侍郎、汴州节度使。虽白刃可胁,岂顾一门;而丹心不移,能怀双阙……公每与从事田僎等仰天望日,裂帛题表,募间道入秦之使,申潜谋破虏之策。”对于常居敌营且无明显正面作为的附逆之人,忍辱负重、暗通款曲、徐徐图之的卧底是最能逻辑自洽的角色。邵说三人的形象塑造,不约而同采纳了这一逻辑。
史朝义于洛阳大败,邵说、王伷趁乱降于唐军。邵说拿出唐肃宗所赐敕书,获授延王府功曹参军,并与王伷在宝应二年(763)六月同时得到唐代宗召见。邵说转述唐代宗说:“卿所进状,朕一一已令检勘,卿之诚节,可谓著明。”寻除王伷侍御史、邵说殿中侍御史。作为封疆一方的实权人物,张献诚的反正真正影响了时局:“及天兵收洛邑……巨寇(史朝义)奔北而受毙,官军自东而势,公之力也。上嘉其忠亮,授特进,试太常卿,兼汴州刺史,防御等使。”张献诚以中原重镇降于朝廷,逼迫史朝义仓皇北窜,对战局的早日结束产生了积极影响,因此获得的官位也是小团体中最高的。宝应二年七月,唐代宗改元大赦,在《册尊号赦文》中点名褒奖了“李宝臣、薛嵩、田承嗣、张献诚等,各与一子五品官并阶,仍加实封二百户”。三人之中,唯有张献诚对朝廷的“功绩”是确切可查的,在战后初期与日后的河朔雄藩相提并论。然而,他的反正是穷途末路之际的“自保”,抑或是潜伏多年以后的“起义”,由于缺乏证据难以判断。
在大规模官员反正浪潮和朝廷宽大优容的氛围中,安史之乱正式进入了历史。
邵说三人回归朝廷后,都飞黄腾达,得以善终。张献诚是三人中职位最高,历任梁州刺史、山南西道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剑南东川节度使,检校户部尚书知省事等,大历三年(768)九月十五日因疾逝于长安光福里,享年46岁。王伷后入汾阳王郭子仪幕府,历任河东县令、河东少尹,回朝累升尚书郎中,大历十四年(779)在太子左赞善大夫任上因疾终于东都私第,享年66岁。拜相失败后,邵说于建中三年(782)受牵连从太子詹事任上贬为归州刺史,建中三四年间“卒于贬所”,享年不详。《新唐书》评价张献诚“喜功名”、“随方制变”。这个评价用在邵说身上,大抵也是成立的。
三、邵说典籍形象的塑造
安史之乱不仅改写了大唐王朝的命运,也割裂了身逢其中的士大夫的人生。“附逆”成为邵说等人挥之不去的隐痛,正如邵说自辩“臣顷陷凶逆,大节已亏,虽昔曾献款,而罪难自赎”。然而,他们最终还是成功地在两唐书中淡化了附逆经历,并且在墓志、奏表中塑造了对朝廷忠心不渝的忠臣形象。单看传世史籍而不细究深意、并辅以相关人等的墓志,“安史剧官”邵说极可能隐身于历史的幽深角落。
两唐书的邵说形象是如何塑造的呢?
安史之乱平定后,唐朝舆论对附逆诸臣相对宽容,而将崔器、吕諲等主张严惩的大臣视作酷吏。“諲用法太深,君子薄之”;《旧唐书·崔器传》记载了一个看似荒诞不经却颇能折射舆论态度的故事:“上元元年七月,器病脚肿,月余疾亟,瞑目则见达奚珣,叩头曰:‘大尹不自由。’左右问之,器答曰:‘达奚大尹尝诉冤于我,我不之许。’如是三日而器卒。”这则故事广为流传,直到百年之后修编《旧唐书》之时。这说明舆论通过对“严惩派”报应不爽的传播来表达对附逆官员的同情。《新唐书》更将崔器列入《酷吏传》,与索元礼、来俊臣同流。
中晚唐之所以会产生此等舆论,植根于当时的政治观念。当“忠君”与切身利益冲突时,当“报国”超乎个体能力时,唐代士大夫尚且不需要以前者为先。考虑身家利益和现实情况,不仅是个人的天然举措,也为社会舆论所认可。士大夫面对君权和政局的重压保有个人空间,可视作是贵族政治的遗风余绪。邵说便受惠于这样的政治风尚。出土文献中多有此种政治风尚的遗物。如“公陷在寇中,为元恶所迫……洎思明怙乱,反辱上国,公再为胁从,累迁□定州刺史北平军。”初看志主似乎是遭到胁迫、无奈出仕的伪政权刺史,而其本人其实是“从陷两京,颇称勇力”的安史元从程元皓,可见粉饰之重。另一位参与安史叛乱的人物墓志表述如下:“遇禄山作孽,思明袭祸,公陷从其中,厄于锋刃,拔擢高用,为署公云麾将军,守左金吾卫大将军,俛仰随代。”看似少有粉饰,但平淡的文字将叛乱经历娓娓道来,除了例行公事般的敷衍态度外,已将忠奸是非置之事外了。
晚唐的动荡,也有利于邵说形象的虚饰。羸弱的朝廷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中无法像唐前期那般组织大规模的典籍修撰。雪上加霜的是,长安、洛阳等政治文化中心屡遭战火,有限的当代典籍、珍贵的原始档案在烈焰中焚为灰烬,殊为可惜。后晋启动《唐书》编修工程之时,只寻到了唐高祖至唐文宗诸朝实录,武宗实录仅余一卷,宣宗以后的实录迄未成书。他们寻到的前代国史仅是韦述所著国史,该书终于代宗朝(其时安史乱事尚未尘埃落定)。大量安史之乱及乱后初期的原始资料早已化为乌有。因此,《旧唐书》有关唐代后期历史的编撰较为棘手。后晋史官只得征集民间史料作为史源。其中人物传记的史料,后晋请朝野官员搜集家史家传、族谱族图等进献。这些史料除了当事人后代的粉饰之外,即便秉持中正之心的材料也是中晚唐政治风尚的载体。大批类似前述出土文献的材料,汇入了《旧唐书》编撰的史源。
当日与王伷同为河南道采访支使的赵晔,同样投降安禄山,《旧唐书·赵晔传》无一字提及赵晔在安史阵营的作为,而是通过一件“善事”说明赵晔守善如初:“时有京兆韦氏,夫任畿官,以不供贼军遇害,韦被逆贼没入为婢……晔哀其冤抑,以钱赎之,俾其妻置之别院,厚供衣食,而晔竟不面其人。明年,收复东都,晔以家财资给,而访其亲属归之,识者咸重焉。”后人读史至此,很容易忽视赵晔本人即是造成韦氏悲剧的“逆贼”之一。有关赵晔附逆的只有“乾元初,三司议罪,贬晋江尉”一句,几年后赵晔仕途稳步升迁。赵晔传记的史源,极可能是后晋史官征集的赵晔利益或情感相关方提供的材料。同时,《旧唐书》记载“晔敦重交友,少时与柳芳友善”,而柳芳又是韦述所著国史的编辑整理者。他的“黑料”不太可能出现在国史中。两项合力,赵晔在唐书中获得了“亡殁,服名检者为之叹息”的正面评价,并列入《忠义传》。随王伷、赵晔附逆的还有判官李承,“承在贼庭,密疏奸谋,多获闻达。两京克复,例贬抚州临川尉”,建中四年卒于湖南都团练观察使任上,并获“承忠悫谋议,勤劳尽瘁,方之者鲜矣”的上佳评价。
邵说经历了与赵晔、李承类似的形象塑造过程。《新唐书》邵说传内容富于《旧唐书》。增加的内容主要引自邵说的《让吏部侍郎表》。与其说补充了史实,毋宁说保留了邵说的“辩白书”。北宋编修《新唐书》时,距离后晋修史又过去了100多年。北宋史官并未寻觅到新的原始资料,而是采纳100多年来新出的笔记、小说、行状、家谱乃至野史材料。邵说的让表当是北宋史官新接触并采纳的。
根植于唐朝中后期的政治风向,再得益于两唐书史料征集的局限性,邵说最终完成了从“安史剧官”到寻常文官的形象塑造,基本漂白了附逆历史。